我喜欢看炊烟,一缕一缕在风中慢悠悠地飘,感觉自己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只是这种感觉并不美妙,我左脚一抬,右脚一滑,还没起飞,就掉进烟囱了。
槐树沟的土窑洞多,这家烟囱在那家院墙外,那家烟囱在这家小路边。烟囱深,出口大,像漏斗。若是横过来,能容一头牛。掉进烟囱的那一刻,不爱说话的我大叫了一声,歇斯底里的那种。突然,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胳膊,向上提,我就有了飞的感觉。不过,只是飞了一下,就摔在地上了,生疼生疼的。我哭了。我的哭声太大,引来全村人。
我上来了,抓我上来的大手不见了,烟囱也不冒烟了,堵了。堵烟囱的应该是救我的那个人。这人是谁?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村邻们有办法,一家一家查对,人都在。那掉进烟囱的人是谁呢?有人质疑,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人掉进去呢?那会儿,我不哭了,用五岁半的声音说:“玉环。”我的话似乎响了点,引来所有人的目光。那目光交织在一起,像一束光,带着风,热辣辣地喷过来,能把我融化。
我说的玉环不是玉,也不像环,是槐树沟的女人。当然,玉环的长相不在闭月羞花之列,就是一个村妇。村邻都说玉环不好惹,谁看见谁烦。可我不这么认为。于是,村里人就说我傻。不过,我也真傻,头大,身子小,遇到人都是死盯,没话,顶多“嘿嘿”一笑。
按辈分,玉环是我婶,可叫玉环婶有点别扭,就直呼玉环,更好听。玉环婶常常绷着一张脸,唯有我叫玉环时,她才咧嘴一笑。
村里的后生们娶媳妇,要设宴款待村邻。槐树沟有个风俗,婚宴吃饭的碗,谁吃谁拿走,带回家。玉环初嫁到槐树沟,扯掉红盖头,拦在大门口,“你们都把碗拿走,我家用啥吃饭。”她双手叉腰,手指乱舞,又说:“你家不娶媳妇了?”村邻们愣住了,一个个嘟囔着,不情愿地把碗放在桌子上。
我把碗塞进背心里,像个不成熟的孕妇。我仰起大脑袋,一脸认真地说:“新媳妇长得真好看。”玉环双手捂嘴笑了,村邻们也跟着解嘲似的大笑,我乘机跑出大门口。槐树沟多少年的风俗被玉环给弄丢了,她的名字被村邻们沉在心底。村邻们满腹心事,刚过门的玉环就这样子,槐树沟以后的日子就是鸡飞狗跳墙了。
烟囱口围满了人,一个个伸长脖子往下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偶尔有烟尘飘上来,呛得村邻们纷纷后退。
每年九月九,槐树沟人有吃油糕的习惯。三婶没油,去玉环家借。玉环让三婶在炕头上坐,打开坛子给三婶盛了一碗麻油。秋后,三婶榨了麻油,来玉环家还油。玉环的手指在碗沿上比画了一下,黑着脸说:“我借出的麻油离碗沿一指高,你还回来的离碗沿两指,少了,不行。”三婶的脸红了,红到脖颈,扭头回家补上。
三婶是个“大喇叭”。村邻们不想惹麻烦,都让着,可玉环没惯着。三婶逢人就说,玉环乘她不注意,把麻油喝进肚子了,又说玉环用小碗借出,用大碗收回,还说玉环的碗端得不正。我举着大脑袋,一旁听着,不说话,“嘿嘿”笑。我担心三婶听不见,提高嗓门,多笑了几声。三婶瞪着眼,“傻瓜,你懂啥,滚。”我没滚,不再笑了,死盯着三婶。三婶干咳了几声,说忙,就走了,走得好快。
我风也似的跑回家取手电筒,递给三婶。三婶嫌弃地看着我,随手朝烟囱里晃了几下,“哪有人?你个傻瓜!”就把手电筒塞在我手里。我手小,攥不紧,差点掉进烟囱。
那年头,日子都不好过,我家更穷。说是看炊烟,其实我是想闻一闻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饭香。路过玉环家,只要她看见我,一准儿会给我半个窝头,或者一个滚烫的煮红薯。她的脸上总是爬满汗珠。她是槐树沟唯一不说我傻的人。
春播的时候也是槐树沟青黄不接的时期。玉环又给我吃了一个煮红薯。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今年田里种什么好呢?”在玉环面前,我没有语言障碍,几乎是脱口而出,“栽红薯,红薯甜,好吃。”玉环笑了,我也笑了。我的笑声不是“嘿嘿”,而是“呵呵”。
入秋,还没开镰就要开镰时,下了一场冰雹。槐树沟人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冰雹,鸡蛋一样,铺满田间地头。糜子谷子高粱玉米就剩光秃秃的秸秆在风中摇曳。红薯藏在土里睡觉,啥事没有。玉环家大丰收。
我喜欢看炊烟,玉环仍旧给我吃煮红薯。玉环站在村口,喊了一嗓子,“一人一筐红薯,来我家取。”喊完这一嗓子,想了想,感觉少了什么,又喊了一嗓子,嗓门更高,“不白吃,哪年你家收成好,还我。”玉环的嗓门真高,我是捂着耳朵听的。这一次我没说话,哈哈大笑,笑了好长时间。玉环弯下腰,拍拍我的大脑袋,估计也想叫我一声傻瓜,却没叫出口,匆匆赶回家了。三婶没有取红薯,是玉环送过去的,多送了一筐,说那一筐不算数。
我知道村邻们不会理睬我。我拿着手电筒,趴在烟囱口,往下照,看见了玉环的花格子布衫。我哭了。好像是哭声惊醒了玉环,她举起手,无力地挥动。我扭头看,三婶拿着一根麻绳,一头系在腰间,另一头扔进烟囱。
玉环离开烟囱的那一刻,我不哭了。我脱下缀满补丁的背心,一遍又一遍擦拭玉环脸上的烟炱。我傻里傻气,不会说感谢的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烟炱遮住玉环的光。
协办单位:广东省小小说学会、河南省小小说学会、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北京键川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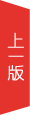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