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数据,202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外卖女骑手比例一般低于10%。但这几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发现,从一线大城市到三、四线小城市,女骑手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增长更快。她所在的课题组在对北京的外卖员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2020年,北京的外卖骑手里女性占9.04%,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6.21%。
这是一群不算年轻的女性,大多在30岁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来自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周边省市的农村,干外卖前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甚至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孙萍接触过的女骑手里,大约70%的女性来自工厂、家政、农业生产等传统行业,剩下的30%是“五花八门、充满有趣故事的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让这个群体的来源更加丰富。孙萍见过不少从旅游业、教培行业转行而来的女性,也有人曾是家庭主妇,因为丈夫公司裁员或降薪,不得不寻得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如果要为她们找到一个共同点,坚韧、有生命力或许是一个,在处境艰难中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希望,并敢于打破常规。
外卖行业综合了高强度、高回报和高压力,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孙萍告诉记者,送外卖本质上是一个体力活,高强度、高压力,人在短时间内要消耗大量体能,男性从生理上比女性更有优势;其次是技术层面,系统的派单、考核、奖励,都对体能占优势的男性更友好。“如果要给这套算法一个性别的话,我觉得是‘男性算法’,女性在里边就是‘闯入者’的角色。”
200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25岁的内蒙古人田蕾(化名)和丈夫来到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村子,做狐狸、貉子的养殖和售卖生意。夫妻俩还到镇上的一个零件厂打工,拿计件工资,合计一个月能挣8000元。两份工填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2012年前后是生意最红火的几年,田蕾的养殖规模一度达到了200只,一年的纯利润有三十几万。
2013年,我国暴发H7N9禽流感病毒,田蕾感觉接下来几年的证件检查、卫生检查日益频繁,皮毛价格也在慢慢跌落。到2016年,养殖场坚持不下去了——在田蕾赔光了向亲戚和信用社借来的十一二万元之后。她是个“不喜欢欠钱”的人,当务之急就是挣到现金还债。“在大城市里跑外卖能挣一万多,还不会被拖欠工资。”最着急用钱时,春节回老家的同乡给他们支了招。2017年,田蕾和丈夫先后来到北京,加入这个陌生的行业。
外卖工作正在为不少处于生活低谷的中年女性提供一个“落脚点”。40岁以上的女性同时面临“高龄”“女性”两项劣势,往往是最先被职场抛弃的。“虽然社会上讨论过,外卖系统如何困住了外卖员,但至少这个大门仍然对这些中年女性敞开”,并给她们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
尽可能抹去女性特征,加入赛场角逐,是大多数女骑手的选择。但不管怎么努力地用时间去弥补体力短板,总有一些困难是“女骑手”难以克服的,比如远距离订单。跑单过程中,如何找到厕所也是个大问题。不过,女骑手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们更细心,出错的概率更低,也有女性特有的体贴。
作为妈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女性骑手往往主动背负起更多的家庭责任。采访中,许多女骑手都会提到,自己会在跑外卖的间隙抽空给老家的孩子打电话,孙萍甚至见过,有女骑手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
跑外卖的第二年,田蕾和丈夫就把十几万的外债还完了。但她并没有轻松下来,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给女儿存“嫁妆钱”。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1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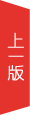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