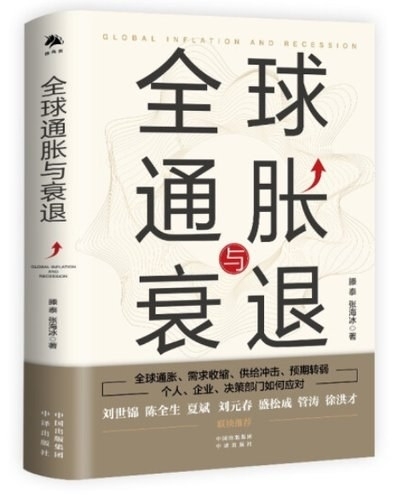超发货币就像上游流下来的洪水,如果沿途被大大小小的泄洪区分流,就不会造成下游洪水泛滥。过去十几年各国超发的货币大部分都被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央行的各种蓄水池分流。然而,与10年前相比,如今很多泄洪区已经变成地上河。
资本市场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纳超发货币的一个主要泄洪区。
2006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是19.29万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冲击,一度下跌至2008年底的11.47万亿美元。在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下,美国股市很快收复失地并创出新高。显然,相对于总规模为6.2万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消费市场,总市值已经突破48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在吸纳过剩美元流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连续多年的上涨,使美国股票市场的估值也已经创下历史新高,成为高悬的地上河。
中国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数量超过5200家,2020年底总市值约80万亿元。
中国股票市场究竟吸收了多少过剩货币?10年前我们曾对2000-2010年累计流向股市的货币量进行了测算,结果是那10年流向股市的资金达到近10万亿元。到2020年底,国内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约80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了1倍多,股市吸纳的资金大约为20万亿元。
考虑到上证综合指数与10年前相比只上涨了20%左右,显然流到中国股市的资金并没有带来股价的持续上涨,市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新公司上市和老公司新增股票发行。由于数千家上市公司的上市所造成的股市大扩容,中国的股票并没有像美国股市那样“涨上天”,从估值和后续排队的拟上市公司融资需求来看,似乎还可以承担更多的蓄水池功能。但是从证券化率(总市值占GDP比重)来看,其市值扩张也是有边界的:2020年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已经达到72.93%的高位,逼近2008年73.35%的历史高点,2021年更是创出了88.84%的历史新高。从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来看,虽然与美国仍然有较大差距,但2020年达到17万亿元,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自从2015年由于大量杠杆资金违规入市造成暴涨暴跌的“股灾”之后,人们对中国股市的看法越来越多地将上涨视为风险,把下跌叫作“风险释放”,认为股市越在低位越安全,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监管政策的取向,在这种观念和政策背景下,利用中国股市继续大量吸纳过剩货币的功能显然不能同欧美相比。
房地产市场
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都是吸纳超发货币的一个主要泄洪区。
对于中国来说,股票市场的资金吸纳能力与美国股票市场相比有差距,但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吸纳能力不可小觑。据测算,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为62.6万亿美元,明显大于美国的33.6万亿美元、日本的10.8万亿美元、英法德三国合计的31.5万亿美元。
如果从商品房销售金额来看,与1987年中国启动住房市场化改革时相比,2020年增长了1577倍。在1988-2020年的32年里,绝大部分年份实现了10%以上的增速,甚至有五年增速在40%以上。20年来中国累计吸纳货币流动性在50万亿人民币以上。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处于“水满则溢”的临界点,指望楼市再度充当超发货币的泄洪区已不现实,房地产市场对超发货币的吸纳能力也不再能与以往相比。
央行蓄水池调节
央行作为货币投放和回收的主导者,可以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缓解流动性缺乏的局面,还可以通过从市场回收流动性,吸收、蓄积过多的流动性。
在2007-2011年间,中国央行运用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将外汇占款增加导致的货币超发回笼冻结在“存款准备金”这个蓄水池中,其中2007年最多,上调了九次,幅度达到五个百分点。2011年5月、6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多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最高达到21.5%的历史最高点。
2000年底,央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同期中国商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2.4万亿,据此计算商业银行上缴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余额为0.74万亿元。截至2011年6月,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8.6万亿元,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提高至21.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已达18%,据此,存款准备金余额约15万亿元。由此不难看出,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18%,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两倍,所吸收的绝对金额则提高了近20倍。加上发行央票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在2001-2010年的10年间,央行蓄水池吸收的基础货币总量就接近20万亿元。2012年以来,中国央行更多通过发行和回收各种短期票据的方式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货币流动量,央行蓄水池的调节力度更加平滑。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