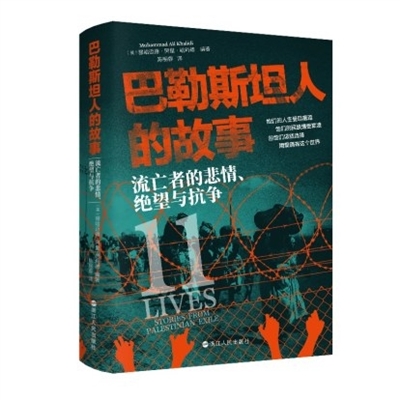无法继承的房子
我周围的所有女性都戴着头巾。奶奶直到70多岁仍然戴着头巾,但这一点不影响她与爷爷之间的眉目传情。我的母亲也戴着头巾,那些层层叠叠地垂落下来、色彩鲜艳饱满的头巾把像波浪般卷曲的浓密头发包裹起来,遮住了女性身上最美丽的部分。
第一次戴着头巾拍照时,我站在白色的背景前,微笑地看着镜头。照片冲洗好后,我把这张照片和一枚刻有“如果可以把我对您的思念当作礼物,我将把它送给您”的句子的钥匙扣装在一起,寄给了父亲。
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学校的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进去后,我看到像巨人般高大的父亲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我扑向他的怀抱,脸上的皮肤却被他浓密的黑胡子所刺痛。
为了庆祝父亲回来,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父亲带我去了我们的新家。
在认识到已不可能回归到巴勒斯坦的事实之后,爷爷用父亲在海湾工作期间赚回来的钱在两个难民营之间购买了一小块地,在上面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自从黎巴嫩发生了巴勒斯坦人的流血事件后,这座房子就成为来自各个派系、民兵和团体的人的庇护所。
母亲是第一个看到那栋新房子的人。她说当她走进去时,几乎晕倒了。对此,我能够想象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沮丧和失落,尤其是当她想到我们在海湾安稳的生活被一群贪婪的士兵和那些掠夺我们财产的人摧毁时。爷爷把房子登记在他的名字之下,然而,在拉菲克·哈里里任黎巴嫩总理期间,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项财产法,禁止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购买和拥有私人土地,因此爷爷去世后,他的子女们无法继承房产或将房子登记在他们的名下。
悬在半空中的自己
读完初中后,我进入塞达市的女子公立高中就读。高二时,我和我的黎巴嫩同学共同获得优秀学习奖。但我从未明白,明明只有我才真正有资格获得这个奖,为什么要让我和那位同学共享这一奖项。
由于身份问题,我经常感到自己悬在半空中。我从未理解在大学里加入巴勒斯坦学生协会、加入某个组织、参加抗议游行或效忠于某个领袖的价值在哪里。也许在我看来,对巴勒斯坦的归属感只是一种私人的情感,是一件私事。我对家乡的热爱和我向真主祈祷的方式很像。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会把那种热爱隐藏起来,只在心里默念。但是我一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疏离感和不安定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
即使我大学毕业并在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建的学校获得一份工作,情况也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机构的存在让我感到羞耻,我有这种想法,既是我的优越感使然,也是因为我浓厚的爱国情怀。或者,这也许是因为我一边不敢承认巴勒斯坦无能、贫困和分裂的事实,另一边却又对这份工作高度依赖,极度需要那充分暴露我们一无所有和揭露世界丑陋面目的一袋面粉或一条毯子。但正是这种对贫困的恐惧,我接受了一份在这个机构当代课老师的工作,即使这个机构从剥削和贫乏的视角来看待我们。
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奶奶过去常常唱歌,她会对着枕头、对着大海、对着长长的道路、对着被遗忘的打谷场、对着指甲花和婚礼等一切事物歌唱。但我从没意识到,她唱的一切都与巴勒斯坦有关。
也许是她流利的歌声和无声的泪水教会了我克制,也许是她那温柔的声音带我看到了我的家乡,也许是她给了我一个矛盾的巴勒斯坦人形象:既是温和的,又是被诅咒的。的确,我指责巴勒斯坦人自己参与了占领活动。如果他们没有把巴勒斯坦留给以色列人就好了,如果他们没有投降,我们就不会被迫迁徙。我们为流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尊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妥协逐渐丧失。我们曾经不顾一切地试图确保自己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让步、背叛和背信弃义的严重性。这些行为不断地、循环往复地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蒙受羞辱。
当我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一个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被认为是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这使得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像信徒那样向近东救济工程处祈祷。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近东救济工程处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服务。
在那里工作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巴勒斯坦人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他们有心理疾病,情感上吝啬不堪。我把这归结于折磨我们的集体意识并蔓延到我们文化中的恐怖心理。吝啬是贫困和害怕匮乏的结果,而守财奴首先是在感情和情绪上吝啬。
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建的学校是让我得以了解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地方,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尽管我对在学校的日常生活感到愤怒,但他们也让我学会对巴勒斯坦社会中那些会让人愤怒和痛苦的一切,报以同情和感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归属感是有问题的,它带来的是致命的冲突、排斥和抵制。巴勒斯坦派系林立,领导人被追捧,我们的家园在充满伪装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
我真的觉得巴勒斯坦人用他们自己的悲惨处境给世界带来了负担,这种悲惨处境有时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有时不是。当我看到我周围的同事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钱和政治派系的时候,当我发现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却在他们的谈话中完全缺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起义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针对自己,反思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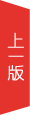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