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会
我初次见到屠岸先生,是在1978年的秋天。其时,他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几个月前,我刚从国家版本图书馆研究室调入人文社,后来被安排在现代部的“五四文学”组,做助理编辑兼《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业务秘书。
当我走进的时候,屠岸先生正坐在靠窗子左边的写字台前埋首看稿。我在他对面椅子上坐下后,他先问了些我的情况,接着,他又耐心地把“五四文学”组各位老同志逐一向我介绍了一遍。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好好地向老同志学习。
我到“五四文学”组工作不久,屠岸先生就担任了人文社的总编辑。记得,我每次走进总编辑办公室的时候,都能看见屠岸先生正伏案忙碌着。有时候,书稿经初审、复审之后,还留有瑕疵。他见到我时,就会细心指出来,嘱咐我以后要留意这方面的问题,等等。直到一切都妥帖了,他才会在《书稿报告》的终审人一栏,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和屠岸先生在一起,如拥暖阳,让人觉得愉悦而温暖,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生出一种尊敬和亲近的感情来。
引 路
1978年秋天,人文社成立了《朝花》儿童文学丛刊编辑室。当时,我初为人父,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幸运地迎来了诗神的降临。于是,就在一种32开的小便笺上,随手记下了一些所思所感。我给最初的几篇起了一个朴素而美丽的名字:《婴儿的诗》——这也是我平生写出的第一组儿童散文诗。我把习作拿给《朝花》的编辑去看,希望得到行家的指教。没想到,这组习作很快就刊登在了1980年6月出版的《朝花》第2期上。
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在人文社西侧的朝内菜市场买好菜,正要回家,迎面就遇到了刚走进市场的屠岸先生和夫人章妙英老师。他告诉我说,已经读过了《朝花》上的我那组儿童散文诗。他鼓励我说:“《婴儿的诗》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先生的鼓励,让我对自己的文字有了自信。
1999年6月,我的第一本儿童散文诗集《星星·月亮的梦》,出版了。收到样书,我首先给屠岸先生寄上一本,请他指教。先生在回信中说:“你的儿童散文诗是你与儿子共同生活中思想感情交流而激发灵感的产物,是你本人带有童心的真情的流露。我想它会得到儿童读者的欢迎。”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够在创作上不断精进。
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屠岸先生创作和翻译的儿童诗。后来,我陆续读了屠岸、方谷绣翻译的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以及屠岸、章燕父女编译的《瞧不见的游戏伴儿:英美著名少儿诗选》等优秀儿童散文诗作品。这些童诗的名作名译,激发起我继续创作的欲望与灵感。
2009年6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我的三本儿童散文诗集。拿到样书,我立刻给屠岸先生寄了一套。先生很快就写来了回信。从先生诚恳的话语里,我体会到了前辈诗人的拳拳爱心,和对年轻人的殷切瞩望。
真 诚
2015年夏初的一天,我到和平里看望屠岸先生。那天上午,先生精神矍铄,谈兴很浓,还送了不少自己的诗集给我。回到家里,我便如品佳酿般阅读起来,并即兴写了一篇小文。几天后,听说一位同事要去先生家,我便请其带上小文,向先生请教。几天后,收到屠岸先生的一封挂号信。
这封信,是写在一页400字的稿纸上的。在信笺右上方,有特意用红笔写出的一行小字:“这是我的重外孙女(不到三岁)涂的。”我把目光,沿着字迹下面的一条红线,转到信笺的左边。这才注意到,那里有两道黑色的划痕。若不是先生特意指出,这划痕一定就被我忽略掉了。年逾九旬的屠岸先生,就是这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对我这个晚辈,也如此尊重。
然而,更令我难忘的是屠岸先生对于文章写作的严格要求,和对后辈的谆谆教导与热情鼓励。先生的教言,主要有三点:一是,“真诚”;二是,要“带着感情写”;三是,要能“打动读者”。这看似简单的三句话,实乃老人家一生写作的经验之谈,堪称文章写作的箴言警句。 (摘自《传记文学》2022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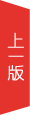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