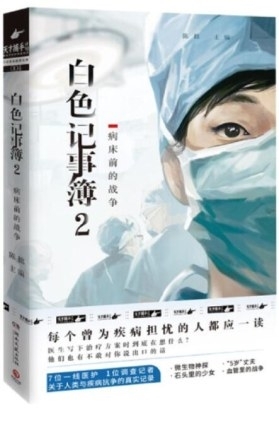本书记录的12个真实故事,是12个罕见、疑难和危重病人的艰难求生路,更是医者与死神的博弈,从中你可以看到从未见过的疾病和人生,经历一场医者和病患为生命而奔赴的战役。一本白色记事薄,承载着生命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恨。
那年盛夏,小希靠着病房的床头坐着,条纹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1.65米的个子,体重只有30公斤,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着,一根根清晰可见,如同一具骷髅。
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翻开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他的病因几乎无解。他们一家辗转数家医院求医,却始终没有一家医院诊断清楚病因,小希只能靠一直服用大量的抗结核药,甚至是激素来减缓病情。一年以来,他经历了几次暴瘦,已经快20岁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而且最近一个月又开始高热不退。
看到小希的肺部CT片时,我彻底绝望了:他的左右两片肺叶布满了小结节,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撕咬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尤其是左肺,几乎被掏空了三分之一。
外院给小希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最大的嫌疑就是结核病,而小希正在服用的五种药物全都是抗结核药,病情却依然没有半点好转。
这时候我想起了医院里的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检验科微生物组是官方全称,我们自己人都称呼那里为“细菌室”。早在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称号——“微生物神探”。
王澎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她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病。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王老师紧接着又问了很多问题,比如病人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与否,皮肤有无破溃等等。但接下来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蒙了:“病人吃过竹鼠吗?”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但王老师告诉我,必须搞清楚这一点。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老师带去了结果:小希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一下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测,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不能第一时间下结论,直到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交了一些底:“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九个病患,之前的八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她曾经诊断的那八个人里面有多达五个人的骨头被啃噬,两个人皮肤上“长毛”,最严重的一个人甚至大脑里都开始“发霉”。王老师报给我一个惨烈的数据:五个病人幸存,三个病人去世。这在感染类的疾病里已经算是极高的致死率。
病菌神秘的面纱已经被揭下了,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可能每个人对真菌都不陌生。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饭菜腐烂后长出的绿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才会显得异常恐怖。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随后在血肉里蔓延,逐渐侵蚀全身,皮肤、内脏、大脑、骨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食物。
王澎老师说:“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在人体内,温度为37摄氏度的时候,它呈圆形或者椭圆形;而在25摄氏度室内温度的环境下,它的周身就会慢慢伸出触角,变成毛茸茸的菌丝形状。所以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上一篇
上一篇